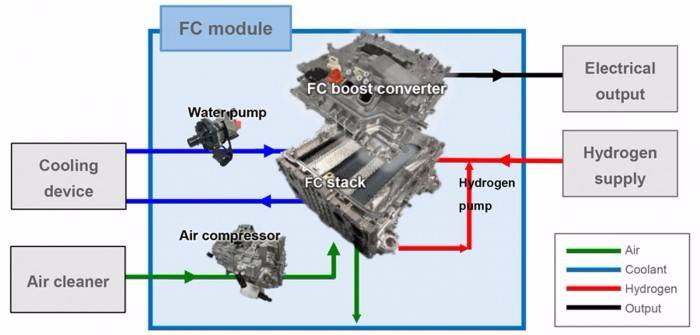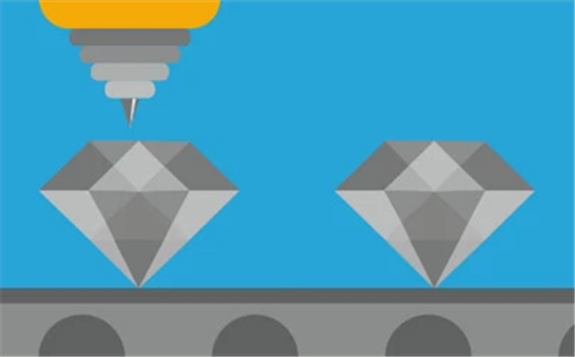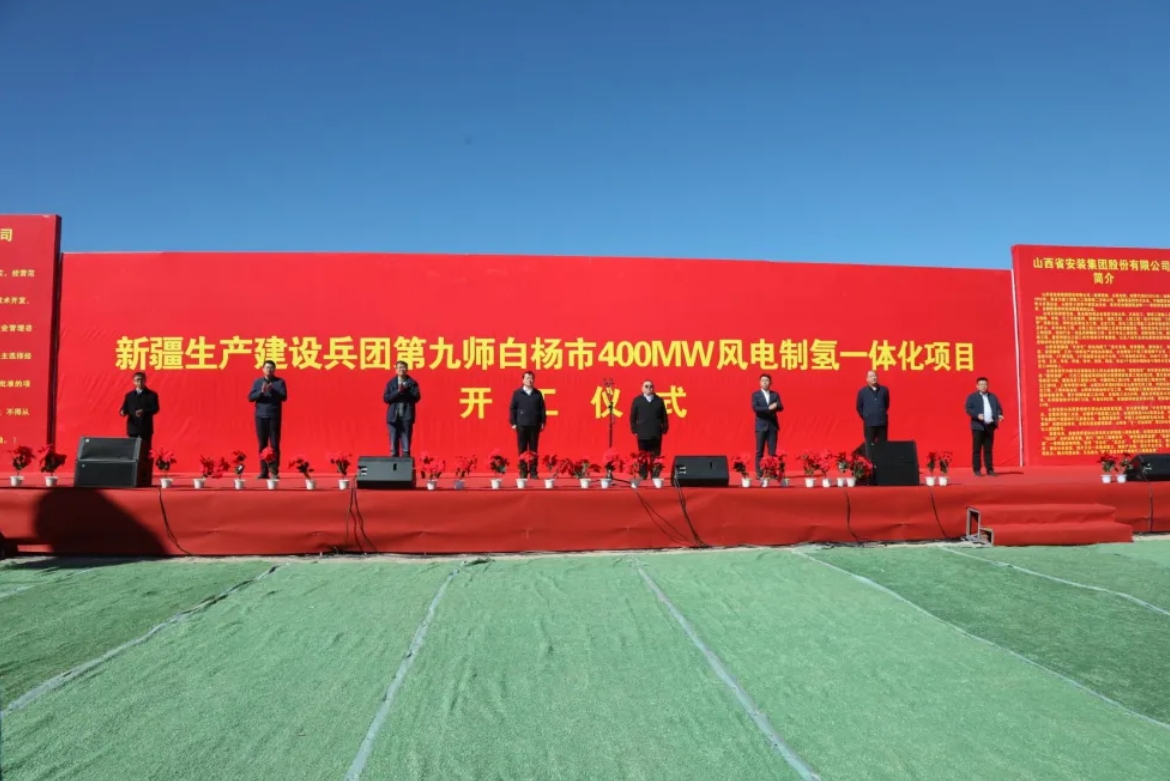日本的“后核能”時代
福島核事故后,盡管民間反核呼聲不斷,但日本核電仍在逐步重啟。2014年4月11日,日本通過了新的《能源基本計劃》,將核能定義為“重要的基荷能源”。2018年7月3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制定的“第五次能源基本計劃”,繼續推進安全前提下的核電重啟。這一計劃還提出繼續推進核燃料循環技術路線的方針。
從2015年8月到2018年底,日本恢復重啟了9臺核電機組。當然,重啟的前提是更為嚴格的核安全改進。事實上,福島核事故后,日本政府吸取經驗教訓,采取了一系列核安全改進措施。
一是優化安全監管機構。在福島核事故以前,負責核電利用和監管的行政機構沒有分開,負責核安全的行政機構也較為分散,導致在對核事故的防備與處理以及保護國民安全等問題上,無法確定到底誰負有第一責任。
福島核事故后日本政府開始著手組建新的安全監管組織機構。將核安全監管職能從經濟產業省分離出來,并與內閣府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進行機能整合,成立相對獨立的核能監管廳,掛靠在環境省。
二是建立和完善法規體系。福島核事故暴露出日本關于核安全和核防災的法律體系以及相關標準、指針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于是,日本逐步實施包括引入新的安全監管制度、強化安全標準、理順復雜的核安全法律體系等針對核安全和核防災法律體系和標準等的修改計劃。
三是轉變防災理念。日本政府已經認識到防災理念存在的問題。這種根本性的改變就是從災害假定向受害假定轉變,這種理念的轉變在核安全管理當中已經有所體現。
例如,日本在修訂《核反應堆規制法》時,明確提出“預想外”的對應措施,認為對地震的預想要考慮得盡量完備,將最嚴重的受害情況考慮在內,在事先做好防震對策的同時要做好受害后的應對。
四是重視對核受害的應對。隨著日本防災害理念的變化,更加重視對核受害的應對。修改《核災害對策特別措施法》,擴充核災害對策總部的副總部長和總部人員,追加在事后對策方面的總部機能。明確核電從業者在災害預防具體措施上具有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五是重視技術、人員等軟環境建設。在技術標準中融入最新的技術達標要求,加強對重大事故的應對以及核災害的預防,制定中長期核能安全措施,強化對核安全預警、災害預防、放射線醫療、核管理等方面專業人才的培養。
六是全面貫徹核安全文化。日本政府通過不斷加強相關部門和工作人員的核安全學習與培訓,杜絕核安全文化意識缺失,貫徹落實核安全文化意識。
對我國的啟示與借鑒
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后,我國核安全監管部門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響應行動,開展綜合安全大檢查,針對薄弱環節提出改進要求;完善核安全工作頂層設計;編制通用技術要求,規范改進行動,確保了我國各項核設施安全改進有效落實,進一步提高了我國核安全水平。
日本福島核事故雖導致核電發展的短暫停滯,但也為核電技術的改進提供了新機遇,對核電與核安全監管提出了新要求。這同樣對我國改進核電與核安全監管提供了啟示與借鑒。
堅持發展核電,確保我國能源安全戰略需求。就目前的技術條件而言,核電能夠長期、穩定地作為化石能源的重要補充。在很多國家的能源戰略中,核電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需考慮滿足高速增長的電力需求,以實現經濟、穩定、清潔、低碳的能源供給。
從人類和平利用核能的歷史看,重大的核事故在短期內對核能利用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從中長期來看,隨著技術進步、監管改進,核電依然是大國能源發展的重要選擇。
確保核電安全,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我國核電發展經歷了起步、適度發展、積極發展、高效發展等階段,但安全始終是我國核電廠建設的第一要務。
我國核電建設均采用國際最高安全標準,在運的核電機組具有國際領先的安全水平,至今未發生國際核事件分級表2級以上事件與事故。核電建設必須以安全為前提,以配套能力為基礎,與設計和設備自主化能力相協調,與公眾接受程度相適應,保證核電建設連續平穩。
完善管理體系,實現高效科學監管。我國應堅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既定方針,即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在《核安全法》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其他核能相關立法工作,進一步完善核電法規標準體系,加強核安全監管,優化改進核電建設全過程安全管理與質量保證,提升核事故應急準備與響應水平。同時,要不斷提高核安全基礎科研能力,發展先進的放射性廢物處理處置技術,提高核廢物的安全管理水平,特別是要攻克高放廢物處置技術,確保環境安全。
探索方式方法,開創涉核公眾溝通新局面。隨著我國核能行業的快速發展,涉核公眾溝通越來越受到各級政府、核能企業和社會組織的高度重視。應推動行業全面貫徹落實《核安全法》,切實履行好公眾溝通的主體責任和相應條款;建立涉核公眾溝通工作長效機制,統籌相關資源,制定工作規劃,優化資源配置,加強區域融合發展;進一步加強行業公眾溝通能力建設,提升我國涉核公眾溝通總體水平;積極推進企業公眾溝通工作的標準化和規范化,卓有成效地開展公眾溝通工作。